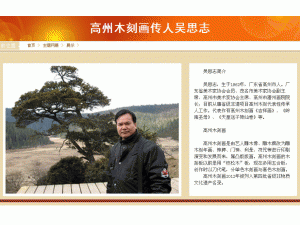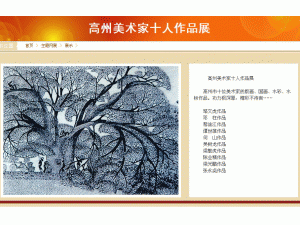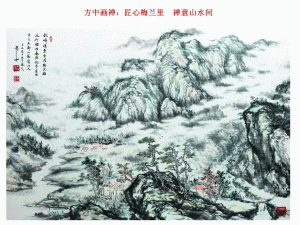|
2010-3-14星期天阴 今天休息。依然是五点半醒了,躺在床上不想起来,一直到七点多,今天早餐坐在床上吃老婆下的饺子。八点半才下床洗涮完毕,随老婆一起到镇上买菜。 小河边的四棵苦楝树开花了。紫色的小花一簇簇拥在枝头,把新绿的叶也衬得淡了。远远的招唤着我。 我信口说:楝树开花了。 老婆:这里没有楝树吧。 我说,你看那四棵就是苦楝树,花开的多盛啊。 老婆:我都没有看到楝籽。北方的树南方少。 走,你不到黄河心不死,到跟前看看。 走到跟前,一股只有楝树花的特有的香味扑袭来。清香中含一丝苦味吧。我反映着枝头的残存的楝籽说,看那不是楝籽是啥。 老婆认可以楝树说。 在另一条小河边,老婆拾到了一颗未枯缩的楝籽,剥掉外皮,用粘粘的糊状的东西,在她细白的手背上重找旧时的记忆。 四十年前没有钱买雪花膏,就用这楝籽剥皮搓手。这个我也用过。四十年前,从湖北江陵小镇回到南阳溧河乡下。日子一下子变了模样。正如冷热浴一样,从热水池猛地跳进凉水里。那份刺激无法言喻,但生活不是洗浴。 冬天天冷,早上的洗脸水是装一碗水放在花拍上,馏馍时,把一碗水蒸热了,一家人就用这一碗水洗脸,洗脸盆只能倾斜着,否则,手就抓不着水。说是洗人就是抓着水,象征性的马眼屎挖掉而已,冰天雪地水寒刺骨,无热水供应,脚基本上不洗的。 如果问为什么这样省水时,我只能回答:没有柴。一年到头分的玉米杆,芝麻干棉花干,只够二个月用,为了柴,野地里草沫都迎风扬后用来做饭了。一到做饭时,家家户户拉风箱的呼踏声不绝于耳。 手脚裂口子渗着血丝。就剥苦楝树籽,用那粘粘的糊状的东西搓他。别说,还真管用。当然还有一招,就是烧热水,把脚手泡透洗净,裂开的口子似乎自动愈合了。 楝树是庄上的主要树种。村东头的水塘边就有十几棵。香山四伯房后就有十几棵楝树。春天来时,繁花如紫云,一团团地炫耀着它的美,那份怪怪地香味,向人们传达的春天的气息。夏天,碎碎的楝树叶遮阴敝日,让我们蹲要树下,边说话边啃着黑红薯面馍。秋天来了,楝籽熟了,一群灰色的楝八哥吵吵闹闹地飞来了,在枝头间跳来跳去,楝籽是它们的美食。楝八哥飞走了,吃不完的楝籽在冬天叶子落尽时,仍然依恋着树枝,在寒风瑟瑟发抖,也不愿落地生根。 楝树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。 在湖北时,我们用竹筒做枪,用筷子缠了布,略比竹筒心粗一点,一头各塞进一棵楝籽,用缠上布的筷子使劲推后面的楝籽,前面的那颗楝籽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,嘭的一声可以飞出去几丈远。 这就是我们的楝籽枪,七八十来岁的我们开心地追逐着,用枪瞄着,嘭嘭的声音不绝于耳。 知道楝树二层皮可以当打虫药还是回南阳后的事。 香山四伯是地主。四娘姓仉,是双铺街的大户人家。四娘的哥还教过我数学呢。 四娘的肚子经常疼。地主婆子的生命那时很贱,而且自己把自己也看得很贱。吃药要钱,哪儿来的钱呢。赤脚医生看说四娘肚里有虫。虫太多了,四娘所以瘦,因为吃的缺,营养跟不上蛔虫的需要,于是虫就^造**了,闹腾得四娘日夜不安。 老人们都知道,楝树的二层皮打蛔虫特别有效。但楝树有毒。一般人少用。四娘的命贱,不怕。 于是她小心用菜刀把房后的楝树第一层皮剥掉,仔细的把第二层薄薄的白色的皮剥下来,放在锅里熬成水,憋着气喝下一大碗。这是真正的苦汤子,苦得嘴都麻木了,只一会儿功夫,四娘额头上冒大汗,肚子更加疼了,疼得大叫。叫得无劲了,疼痛也过去了。有了便意,到茅房里拉出二大团蛔虫。 从此后,四娘的肚子疼病结束了。 用楝树皮打虫,现在是很少听说了。现在的人们也少有得蛔虫病的。卫生状况不同,一些病就慢慢的少了,但新病却层出不穷了。 楝树,儿时的清晰记忆。 |
| 您看到此篇文章时的感受是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