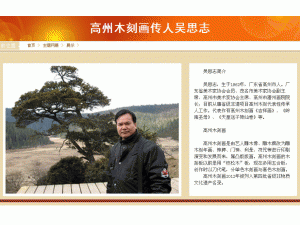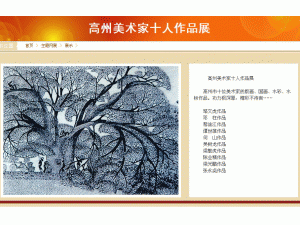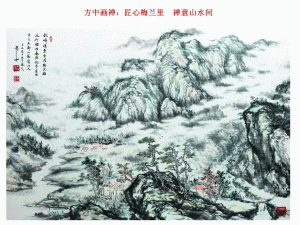|
在村庄,忙乎东西、叫嚣于南北的,永远是那些顽童。他们大多介于七岁至十二三岁之间。他们不一定都是男孩,他们成群结队,永远有一个最顽劣的领着头。 他们整天好斗,村庄里什么东西都倒他们的霉。最先挨整的,一定是那些猪狗和鸡鸭。老家的猪大半是放养,它们鼻子哼哼,甩着小尾巴,四处觅食。和放学的顽童狭路相逢,其中一个便会把黄书包交给同伴,一偏腿便纵上猪背。猪攒蹄飞奔,猪背上的“骑士”居然揪着猪鬃,颠颠地就是不下来,俨然有草原跃马的气势。至于狗,千万不要在路上表演恩爱。如果被顽童们看到一定会治你个流氓案强奸犯之罪,不把其打个遍体鳞伤,是不肯罢休的。 门板在村子里算是最老实听话的吧。消夏的时候,可以卸下来做铺板;需要晾晒什么东西,还可以将它们摆布在太阳底下充当晒席。可就是它们,受顽童的伤害却是最深。他们有事没事,总把自己制作的飞镖、飞刀之类的暗器磨得飞快。在门板当中画一个白粉圈,有时是场比赛,有时是独自单练,霍霍声不断,暗器嗖嗖地往门板上扎。门板伤痕累累,疮疤密布。这也只是门板,换了别的早就哎呦声不止,甚至跪地求饶了。受欺侮的还有屋瓦和窗玻璃,只要一语不合,顽童们一个石头子嗖地就飞了出来。 窗玻璃是应声便碎。屋瓦坚挺一点的,石子会哗哗啦啦从瓦楞间滚下坠地。屋瓦老旧的,会仓啷碎裂,有时候还会殃及屋内的铁锅。 路人也是偶尔可以“欺侮”一下的,但凡听得算命瞎子二胡声响,便有顽童潜伏于其必经之处。瞎子杖着探路的马刀,拉着二胡,哼着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的曲调笃笃走近。孩子王一声呼喝,猛地上前撇掉他的马刀。众顽童呼拥而上,搬脚的搬脚,拽胯的拽胯。瞎子经不住拉扯跌落尘埃,一身蓝卡布袍沾惹牛粪猪屎无数。瞎子作势欲打,坏小子们作鸟兽散,顷刻间踪迹绝无。瞎子抖衣起身,再寻马刀。口里骂声不绝,却不真骂。因为他知道,每走进一个村子,这样的顽童都有。不出意外的话,顽童们的亲属会闻讯赶来,一边大骂顽童,一边帮算命瞎子拍打灰土,而后搀其到住处闲坐喝茶,顺便掐一掐八字或者摸几张命牌,由是他的生意也便开了张。 顽童们干过的坏事远不止这些。经典的还有打枣偷瓜、纸弹弓袭人、轰炸路上的粪堆、编歌谣讥讽对方阵营顽童的身体缺陷、数落人家父母不雅的外号、在洁净的粉墙上糊涂乱抹说小伙伴里谁谁是老公老婆…… 村子里一茬一茬的顽童,层出不穷。像村口老樟树上鸟巢里次第出壳的鸟蛋,这一批爬出蛋壳,飞出窝子。新的鸟蛋又挤挤挨挨续满了鸟巢。 踏着年的脚步,我候鸟一般地回到村庄。一帮顽童唿哨一声,眼前晃过,朝我脚底丢下一个震天响。我在硝烟中抱头鼠窜,而顽童们偷袭成功,远处随风飘来的笑声是那么畅快恣意。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,尽管不情愿,但不得不承认:这个村庄已经不再属于我,虽然我对它日思夜想。 |
| 您看到此篇文章时的感受是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