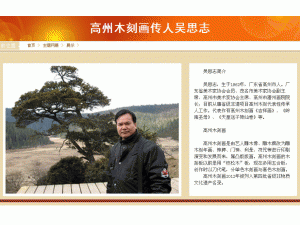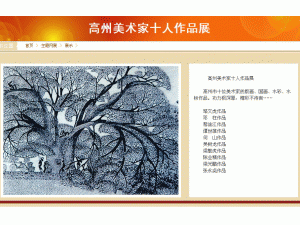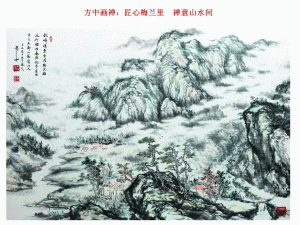|
又上一个大坡,身后是一个喀纳斯河大拐弯,太阳刚好照在山顶上泻落河床中,一半有阳光,一半是阴影。大拐弯正在阴影下,在刺眼的光线下想看清她都难。上了坡顶,路不随河走,竟直走到河边的山顶上,这里少有人走,往河下游看风景绝佳。想到同伴可能不会到处,在这拍的相片也最多。然后下这山,山脚旁边的草地上我们的两个马夫正在等我们,叫他们取下装有食品的行李,拿了一个小哈密瓜,没有刀,用石头砸烂狼吞虎咽的很快就把它消灭掉,又拿了两个香梨,这时盐水和葵到了,为了赶找地方拍日落,也不等她俩,就匆匆上路。 刚吃完哈密瓜的手有点沾,看到旁边有路可以下到河中,于是就沿路下河洗手。河边依稀有一条小路似乎有人走过,我想可能这路会走到前面与大路汇合。这样抄近路会省许多力气,于是决定沿着河边走下去。开始,还可见到盐水和葵在山上大路行走的身影,还听到她们叫我上来。我也想上去和她俩汇合,但没有路,又不想走回头,只能往前走。河又碰到一个拐弯,前面又有悬崖峭壁。此时已看不到太阳,一个人翻山越岭走在峭壁上真的有点怕,双手抓在一些和知名有刺的植物上,留下了满手的刺,很痛,但理不了那么多。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出大路,精疲力尽,也见不到同伴。再渴再饿再累也不敢停下休息,我得追上大部队呀。所以仍是走得飞快。 过了不久,老想追了上来,说缘,帘和老痴还在后面,两人结伴走到三角洲,又追上了盐水和葵,她俩问过人了,三角洲已住满人,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继续朝前走了,据说离此一个多小时路程的地方还有另一个宿营地,他们已走向哪。我们也只有继续往前走,虽然此时双脚已是铅般的沉重,机械似的挪动着。天已快全黑,老想说要先行一步追赶先头部队,说完就飞奔转眼不见身影。我们剩下的三人速度也不慢,要知道老想是一路跑过来的。也没想到,老想这一和我们分别,使我和两个MM与大部队走失,三人在荒山野岭的黑夜中相依为命,暴走禾木,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驴行旅程。 夜走禾木 和老想分开十几分钟,天就完全黑了。三人走得飞快,想尽早赶到宿营地和先头部队汇合。在黑夜中,我们用上了头灯和手电筒,约走了一个小时,跟本就没见到有什么毡房,更看不到一个人影,这时我们知道我们有可能走错路了。但我估计我们这一走已和他们所说的毡房走离了超过5公里。这时又累又饿又冷,要知道,在未到三角洲之前我的体力已严重透支,现在又急行了数公里,已快支持不住了。 怎么办?我们三人肯定是丢队了!叫停了在前走的葵和盐水,休息的瞬间,三人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。往回走,如果找不到大部队会很惨,行李都由马夫带着跟他们在一起,没有帐篷睡袋,在这零度以下的荒山野岭肯定捱不过一夜。而且,我们也不知先头部队究竟是在后面或在我们的前头。更有甚者,我们当时也担心一个人往前追的老想,不知他有否赶上了先头部队。如果没,他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黑夜中比我们三人更惨。 |
| 您看到此篇文章时的感受是: |